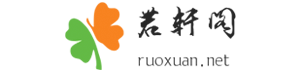好吃的背后,是浓浓的亲情。文末附“法国版包子”食谱,中西合璧更好吃!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ruoxuanlife ,就能天天收到若轩阁的精彩文章了,咱们微信里见!

包子
文/海棠
这次回家发现,我老妈越老,越拿自己当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所有的退休中学老师都这样,退人不退心,更不退职业病?转念再一想,这是她还不老的表现嘛。于是乎,咬紧牙啊,一个月听她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
直到离家前的最后三日。老妈问:“就剩三天了,快说,还想吃什么。”
这次回家。老妈又出新词汇了。从前每次回家,我楼下摁铃,她楼上开门,门边候着,等我上楼,“咚咚咚”,楼梯转角我一出现,还隔八丈远她就吼上了:“你看看你那两条狼腿。你看看你那两条狼腿。”
我一般春天回家。一身春装。
而这次回家是春节。长羽绒服,包到脚背。老妈这样出词了:“你看看你那个小脸,你看看你那个小脸,跟个干辣椒似的。我看你下巴都勾勾了。”
于是乎,我每天的生活,就是从早到晚接受老爸老妈施肥,灌溉,培育早稻田。因逢春节,家里冰箱满地要流出来了,“肥”嘛,也就因冰箱制宜。一日三餐再一日三餐,怎么竟然,只有三天九餐可以吃了?我赶紧说:“没吃上包子呢。”
老妈:“哦!好!中午就包。烫面的,还是发面的?萝卜丝的,还是白菜的?”
我:“发面的。萝卜丝的。”
老妈:“老头,赶快发面。包两天她吃的包子,最后一天吃饺子。”
我:“别吃饺子了。三天都吃包子。”
老妈是个奉行“进门的面条,滚蛋的饺子”之人。我的要求有悖了。这也是第一回。她不懂了,回家一月头一遭,听老妈出了一句谦虚的,不懂之词:“三天都吃包子?包子就那么好吃?”
是的。包子就那么好吃。要不,怎么说她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是自封呢。自己养大的小孩,竟然发如此的不妈妈之问。
记得多年前,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,挪驾法兰西,探望闺女女婿时。对他们的“给你带点什么去”之问,我就一句:“包几个包子带过来吧。”
因是九月末十月初,老头老太太一宿没睡着,第二天一大早给我电话,说:“想了一晚上啊,孩子,这个包子不能包啊,飞机里温度高,包子馊了,十个小时的飞机那个味儿,还有个受?等去了给你包,还不一样吗。”
怎么可能一样呢。法国风土中长大的萝卜,小麦,肥猪肉,跟中国的,一定不一个味儿。
我法国蒸锅蒸出来的包子,和爸妈的老蒸笼的出笼之物,永不相同。
记得我们小时候。老妈已好和别人攀比了。可那会儿,大家都无产阶级。没车,没房,没名表。人也黄脸婆,水桶腰,比英俊潇洒的季节已过。比什么。比孩子。二楼老温家,夫妻两同我爸妈,年纪相仿,职业近似。家亦一儿一女。女儿同我同年。儿子和哥哥同班。我爸妈一天到晚羡慕人家啊:“看看人家的孩子,什么活都会干,饺子会包,衣裳会洗,爹妈下班,饭都给做好了。看看咱这俩。”
挺自豪的一通笑。
我和哥哥也确实。手都笨,啥活都干不好。好容易洗一件衣裳,我妈也像给学生改作业那样,一眼就看出毛病了。她干家务也争强好胜,什么活,她一干就好,我们都不行。
所以,哥哥和我,除了听话,受训,念书,一无所长。
那年暑假,哥哥14岁,我10岁。妈妈参见一个暑期教师进修班。早上出门前,一大盆面发上了,说晚上回家包包子。
暑假日日漫长。爸妈又不高兴我们出门,和其他一孩一起疯。所以,借了无数本书,要求我们一个假期看完。书摞在桌上,歪歪扭扭的一大摞。摊在床上,桌上,东一本,西一本。
我们那时住烟台西山脚下,最后一栋筒子楼。一楼。压在一堵小山坡,加固石墙的长长的阴影里。哥哥住小东屋。我随爸妈,住大西屋。一大盆面随我们,早上在有阳光的小东屋。太阳挪到西屋,面盆跟上,回西屋炕上,它静发,我们看书。横着躺,竖着躺,左侧身躺,右侧身躺,躺着看累了坐起来,坐着看累了再趴下,书上字看着串行,模糊一片时,面悄悄饱胀、变形——睡起来的俩人也像发大的面,前后左右收拾不住,咣咣当当一点点看清了,窗外的阳光,已爬到石墙最后一道缝儿。真像睡一觉人就长大了,一个暑期过去孩子就成年了,我突然说哥哥:“咱包包子吧,爸妈回家就能吃上了。”
哥哥即刻率领我,干上了。
茼蒿洗了,切了,三刀两斧。葱姜蒜,香菜。油啊,酱油啊,醋啊,倒一下,两人争执一番。但最难的,是包。妈妈一向包长的麦穗包,爸爸习惯包碎褶儿圆包子。我们两个人耳濡目染,觉得是包子就一定带褶儿。于是端着裹菜的厚面皮,生拽硬拉,掐一下,再掐一下,包子没出褶,而一排窟窿眼。补救的办法,用面团团堵上大小窟窿。
爸妈下班后,看见儿女给他们包的第一锅包子,如何反应,我一丝记忆也没有了。可是,哥哥一揭开锅,包子大开花,一锅烂蒸菜的镜头,我一辈子不忘。
如今想想,我那爹妈那会子一定,依然照旧,以批评代鼓励,以资进步。所以至今,我反正进不了步,从未自家包过包子,因为不敢掐包子褶的小麦穗。
好在法兰西无包子。这祖辈使刀叉之国,子民们打死也不会舞动十指,捏包子褶的。包子褶这艺术之功,只我们这舞筷子的民族的巧手,才弄得出。哼,还轻轻巧巧,一点不费事的样儿。
真气死人。
也好在“包子有肉,不在褶儿多。”没褶有肉的发面团团,谁敢说,不叫包子呢。饮食制作之道,也贵在创新,老菜新作,中国包子外国包之类的。
譬如爹妈探法的那一次,我就给他们搞了个法国包子出来。和中国包子的主要区别,第一:面。我用千层酥的油酥面,而非发面,亦非烫面。第二:加热手段。用烤箱,而非以水为加热媒介的蒸笼。呵呵,其实这是我所住的法国阿尔萨斯地区,一道地方菜,叫肉塔。顾名思义,全肉馅,——法兰西是食肉民族。
我呢,中国心一起,大量圆葱、大葱白交融而入,——中国人毕竟吃菜多。肉嘛,用小牛肉猪里脊肉各一半。中外各色调料煨一宿。搞成一褶全无的小胖子。出了烤箱金软酥焦,一咬一口的华丽缘。我老爸老妈吃得直迷糊。老妈说:“你这哪儿学的这身本事。”
言外之意,除了她,我胆敢它处拜师了!
我赶紧地:“这哪有你的萝卜丝包子好吃啊。”
此非虚言。老妈包的,所有的馅的包子都好吃。尤其萝卜丝的,萝卜丝、猪肉,虾皮、香菜做馅,让人越吃越想吃。我们山东包子像山东大汉,一个字,大。没出国之前,一个包子我都得好好吃。如今,三四个不在话下。且,同去国时间成正比。出国时间越长,吃的包子个数越多。我个“狼腿”“干辣椒脸”的在老妈眼里,既不“狼腿”,亦不“干辣椒脸”了,一看我伸筷子她就吼,甚至打我筷子,“不吃了,不能吃了!”
我小舅碰巧来了我家,边上听着,不高兴上了。讲吼嘛,他老姐能吼过他?将六十的人了,那嗓门一敞!
“有么呢!你就让她吃嘛。吃撑了出去走走。”
我老爸也缓声附和:“小舅说得对,再吃一个,吃完了和你小舅去烟台山看看花灯去。”
老妈对着老爸就去了:“你就会装好人。”
对着她老弟:“你懂不懂!你懂不懂!人一定不能暴饮暴食。为什么不能暴饮暴食——,你不懂了吧?——中医讲,对心脏、胃、脾都不好。”
小舅:“谁说不是呢。”
拿起最大个的包子,塞我手里。
我用它碰碰小舅的酒杯:“小舅,养育之恩哈。”
童年七年在姥姥家,姥姥姥爷年纪很大了,不能出工干活,挣工分了。一大群姨姨舅舅,出嫁的出嫁,另立门户的另立门户。姥姥姥爷身边只有未婚的小舅和小姨。小姨后来也离家,进城当工人去了,地里活,就全指望小舅一人了。他是家里唯一的整劳力。
我和哥哥,是小舅帮着姥姥姥爷,养育了我们七年。
小舅是姥姥姥爷晚年得子,俩儿子最小的一个。姥爷一辈子总生丫头,一二三四五,这个基因,一滴不漏,全传给俩儿子。大儿子,仨闺女。小儿子,俩闺女。会看相的人看姥爷和我俩舅舅,说他们人中浅短,阴气大于阳气。换句通俗话,全气管炎。换句拍马话,不操心的命。
小舅的不操心如今看,真有成果。一个这把岁数的农民了,活脱一株风调雨顺的钻天杨,洁白的衬衣,笔直的裤线,近60的人了还腰板溜直,头发一丝不花,皱纹几乎不见,浑身上下顺顺溜溜,洁洁净净。从前,我们小时候,他清晨两点起来出猪圈粪挣工分的苦难生活,怎么一痕印迹都不留呢?
哎!气管炎真好命啊。
然而小舅的气管炎是那种非常高级的气管炎。也就是说,他一辈子把小舅妈的“高管”化为“娇宠”。为人极有胸襟,极端低调,面对小舅妈的指令他一向态度恳切地说:“嗯,什么事你一干就比我像样。”“我这个人,就得你这个人给掌着舵,把着方向。”小舅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得益书香的熏染。虽然打小就不爱上学,也就个小学毕业吧。可就是爱看书。如今外孙女抱了好几年,好几个了,还本本不漏地看《小说月报》《当代》……
我小舅妈嘛,自然一辈子累个半死,还死心塌地爱她的甩手大帅哥。小舅年轻时就帅,老了成风度了。真不枉小舅妈不到二十岁就追他,追十年方到手的爱情。
而若说小舅的变化嘛,也还是——有两点的。
第一,轻易不吼话了。
吼话似乎是我们小洛村的祖风。先说男人们,印象里说话全笔直的脖子,面色涨红,如同高射炮用到了极热状态,出口一语,“通”地射上天,喷烟冒气,砸得地上人一头一脸的土渣渣。——侉极了的文登话。而女人们,低声的说笑也极具穿透力,发散力。这个村子史来没出几个歌唱家,不懂咋回事。所以我老妈的吼话,非职业病,而村域特色。那么大嗓门一辈子,若换其他人,早喉炎上了。老妈,近八十还声若洪钟。佩服佩服。
我的小舅,不吼话时,温柔极了。
一声大吼,为了我这个他养育大的老外甥女,多吃几个包子。
第二,饭量明显小了。
山东大包子小舅在我们小时候,他年轻时,一口气吃14个。为了他的到来,包子以外,爸妈备了盛宴,葱爆海参呀,避风塘炸虾呀,红烧扒皮狼鱼呀,芋头炖大排啊——盘盘碟碟,他浅尝辄止。爸妈作风依然,恨不得一桌子菜端起,倒进小舅碗里。小舅边推辞,边说:“生活好了,人就不能吃了,哪像年轻那会,饿捞捞的驴肚子。xx最记事了,你不记得了,你姥包得这么大的驴肉包子——”小舅对着我,一双大手空里一比划,沉甸甸的一大坨,“我吃10个。”
记得。怎么会不记得。“天上的龙肉,地上的驴肉”,我至今只吃过那一回驴肉。而那是七十年代,小舅的话,人人饿牢牢的一个驴肚子,粮食都不够吃,哪来的驴肉包?
生产队的驴死了呗。
那会儿吃饭这件大事由国家来负责。农民的口粮顾名思义由生产队,根据人口分配。吃饭吃个七八分饱有利于健康,我们那会的肚皮,常空一半,呵呵挺养生的。可人的精神境界倒下滑了。小舅领着哥哥和我,苞米熟了偷苞米,地瓜熟了偷地瓜。哥哥和我望风,他钻地里偷。地瓜偷来用湿泥巴裹了,在生产队打麦场的露天大土灶,烧了吃。青嫩苞米棒子也是,火上燎了,喷香喷香的——
吃饱了小舅一蹲身,哥哥窜上他后背,我扒到哥哥身上。哥哥双手后环,扯住我的双腿。我的双臂前伸,抓紧小舅的双肩。小舅长长的胳膊胸前一抄,兜起哥哥的腿,一声喊:“吃饱啰——回家啰——”身一起,长腿一大步迈出去,越迈越快——哥哥和我,双腿悠悠荡荡的。我的的小布褂全扯在肚脐以上,圆溜溜的小肚皮在风里,凉飕飕的。小舅迈一步,我们颠一下——哥哥一起头,我跟着就唱:
我爱北京天安门,
天安门上太阳升。
伟大领袖毛主席,
领导我们向前进——
生产队里我不记得有几匹马,而是牛,骡子,最多的,是驴。驴套大轱辘的木板长马车,田间路上迎面而来。若是我们空捞捞三张肚皮,小舅就驮着我俩站在田埂上,哒哒哒驴啼声中无限向往地自言自语:“驴怎么还不死啊。”
唉!生产队的一匹驴,真病死了。
全村人的振奋,可想而知了。
驴死了,意味着家家户户按人口,要分驴肉吃了。别说驴肉了,猪肉也只有过年才吃的上一回。还不管够。意思意思而已。
如今想想,中华民族真有智慧啊。如果没有包子这个饮食大发明,吃驴肉,无论红烧或炖菜,总得备主食吧,蒸馒头或烙饼,耗时耗力且不说,更耗柴火。
而那个年代,柴火也主要靠生产队分配麦秸啦,玉米秸啦。冬天又冷又长。哪够烧到头的。
所以,那时冬日的田野全干干净净的。连沟边田畴的荒草也被家家户户搂个干净,——补贴烧柴。好在那时的老房子造得极合理,全面阳而坐,厚茅草顶,石砖墙,泥巴厚厚抹了墙皮,窗户小开,吊顶天棚,冬保暖,夏散热。屋子全低矮窄狭。大锅灶连着大土炕,一把火,热一天。
进入冬闲人不必出工下地了,大姑娘小媳妇们扎堆,三五人凑一户人家的热炕头上,绣花,钩花,按件卖给城里的绣花厂,出口,或怎么卖了,挣点钱。青壮年男子,譬如小舅,那时已婚了,去二三十里远的镇上工厂,什么石墨厂啊,盐场啊,打零工。
村巷里弥漫着冬日特有的那种安静。太阳晚晚的出门,村东照到村西,要漫长的时间。阳光把身子拉得长长的,薄薄的。有风吹来,一下子就散了。风里跑来跑去的家狗野狗,鸡鸭鹅,荡荡尘土。家家的炊烟,一日三次的喜欢。
我守着姥爷,在窗下搓草绳。突然看见小舅推自行车,进院了。后车座绑了个鼓鼓囊囊的麻袋,鬼头鬼脑送进紧挨猪圈的小仓房。那里面又潮又暗,窗户也没有,是放农具的。他进那里干什么?他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?
我呼一声推开白纸糊的木棂窗,大声喊:“小舅,你干嘛啊?”
我的小舅急得脸红脖子长,一边直嘘我,一边戳他住的小西屋。
我:“小舅妈绣花去了,早走了。”
小舅释然,招手我过去。
我跑出屋一看,啊!原来麻袋里,躺一只我这么大的小黑猪仔。死了。尾巴硬硬的。一身泥。无需小舅解释我就明白了,他终于如愿以偿了。
为什么这么说?
一点说明。
不知别人家如何,反正小舅和我们,走起路来一向真忙活,眼不闲,心不闲。心里祈愿:哎呀,路边出现个什么好吃的吧,譬如谁掉的一个烧饼什么的。眼呢,自然滴溜溜转,树上的鸟窝,水沟里,路边上——后来离开姥姥家进城,和父母一起生活,倒不是因为“我在马路边,捡到一分钱”的歌声的影响,反正,我从来盯着路面看,希望捡上一毛钱。这种习惯长大后因为马克吐温那篇小说《百万英镑》,直线升级,留学法国更盯着地皮走路,巴望着突然捡上一张大钞票。
无需说明。小舅上班的路上终于看到了一头小死猪。患猪瘟而死。被人扔在路边的水沟里。大喜过望的他窜进沟里正要拣,偏前也人来,后也人来。就此作罢吧,怎可能!当着人面抱着死猪上来吧,多丢人啊。我的小舅是个极好面子之人。那个年代,已然成天价,裤兜里揣面小圆镜子。于是乎,那么冷的腊月天,他就装肚子坏的那一个,在小黑猪仔身前,蹲下来,一拨路人,近了又远了,又几个路人——
“小舅,我就不明白了,小舅妈那会儿就不馋肉?拣头死猪这样的好事,你怎么还怕她,躲着她呢?”
我小舅“嗞”一口小红酒,慢条斯理地说:“她那会儿,不是怀上小丽(我表妹)了吗。”
啊!三十多年后我才明白了。小舅为什么急捞捞的,一听小舅妈不在,马上嚷着,要姥爷别搓草绳了,赶快烧火,他要在小舅妈回家之前,杀猪。这样的话,小舅妈中午回家,看到的就不是瘟猪,而是从天而降的——大——猪——肉。
那么,小舅怎可能不敞开肚皮吃呢。姥姥包的猪肉萝卜丝包子,小舅43码的脚,一只包子,足足小舅一只脚板的大小。一憋气,小舅吃了14个。那种场面的壮观,我自己吃的情况,一点不记得了。
小舅接过老妈递给他的大包子,一掰两半,大半的给我,他吃小半的:“现在可是吃不动了。”
我:“小舅,你说这个包子好吃,还是那个瘟猪包子好吃啊。”
小舅:“肯定那个好吃了。你不知道吗,珍珠翡翠白玉汤。”
我:“小舅,那你说,你爱那会的日子,还是现在啊。”
小舅:“你这个孩子。还用问吗。现在的日子多好过啊。”
我:“哎,小舅,你说说现在若吃一只瘟猪,咱全家还不都,至少住院隔离了。你看那会儿,小舅妈那通吃,可小丽生出来,还是如今的注册会计师。”
小舅:“时代不同了,猪瘟不一样嘛。”
海棠式油酥塔:
300g小牛肉;300g猪里脊肉。切丝。200g圆葱,100g大葱白。切丝。适量香菜,生姜,一只小香葱头(echalote)。切丝。
如上置于容器中,加适量盐,胡椒粉,肉桂粉,丁香酚,几只大料,香叶,百里香。再加雷司令白葡萄酒,已漫过腌制物为准。最后,加一勺白兰地,以质量好的白兰地为佳。
腌制一宿。
取适量油酥面,分为二,擀皮,上下包裹住腌肉馅,长方形,圆形,三角形。入烤盘。用刀刃轻画各色图案。再抹一层蛋黄或鲜奶,益于着色。
烤箱预热250度,焙烤30分钟;将至180度,焙烤15分钟。
油酥鲜美,入口欲罢不能。


(来源)
本文来源于网络转载或用户投稿,不代表若轩阁立场,如有侵犯您的版权,请联系我们,我们第一时间删除相关文章,联系QQ/微信:453160。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ruoxuan.net/6732.html